《香港作家》從港台文學對讀看紀錄片《1918》與《我城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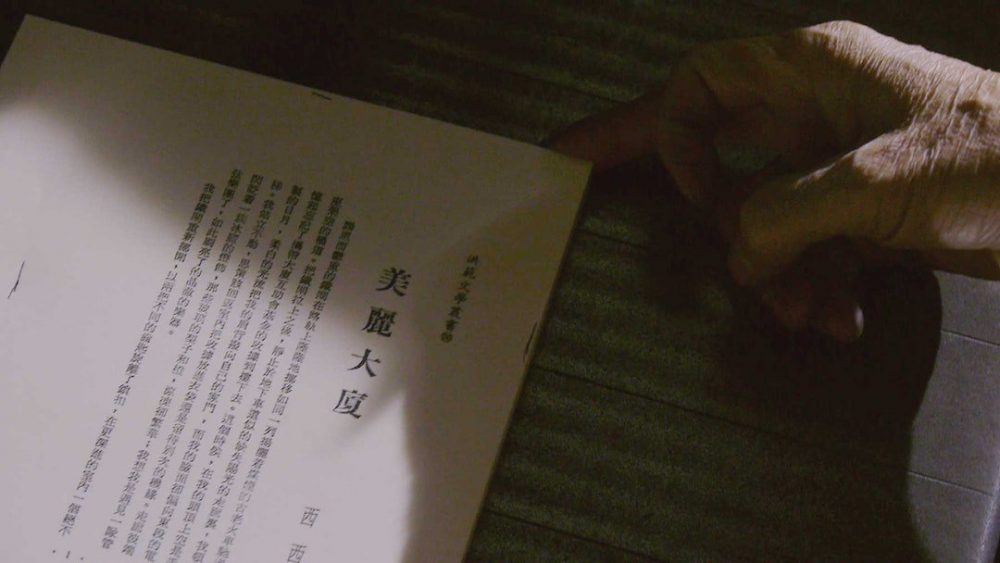
為了替在島上曾經或持續用文字深鑿慢刻的一代造字人留下影像,日常的,魔幻的,生動的,文字與文字以外的種種,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拍攝企劃持續推進。2015年發行的系列二很特別,除了四個台灣作家,紀錄片造舟載著台灣讀者漂向海的另一端憂戚與共的島嶼,選擇三位重要的香港作家作為文學紀錄片拍攝對象。
紀錄片在兩座島上播映。在香港,大概不太可能有人問:為什麼是是劉以鬯?為什麼是西西?為什麼是也斯?無論談多產,或者他們在文學中不斷探問、逼近、包圍出香港城香港人特殊的身世與時空感,特別是西西和劉以鬯對文學形式多年來驚人的實驗能量,跨媒材創作,研究他們的論文豐盛到幾乎可以稱為「劉以鬯學」、「西西學」。所以,如果要列出香港文學代表性創作者,絕對沒辦法略過這兩個名字不談 [1]。
不過,在台灣,特別是年輕讀者,也許對陳果(拍攝西西紀錄片的導演)的《三更2之餃子》記憶猶新,或者熱愛《奪命金》編劇黃勁輝的說故事能力,卻不一定讀過西西的《我城》,可能也不知道劉以鬯小說與王家衛電影的互文關係。關於兩個島嶼之間的文學對讀史,《我城》特別找了馬世芳談西西,回憶1989年他十八歲第一次在書局買到允晨出版的《我城》 [2],原不識西西,一讀卻不得了,被小說舉重若輕的文字質地剖開心臟,目眩神迷,馬世芳後來這麼寫:「很長一段時間,我心目中理想的香港,不是明信片上的維港夜色,而是書裏七十年代那座年輕的充滿朝氣的《我城》。」 [3]不過,台灣青年被香港作家啟蒙之前,1984年洪範出版《像我這樣一個女子》,已經先在台灣刮起一陣以西西體「像我這樣一個⋯⋯」起頭造句的風潮,紀錄片也訪問了負責人葉步榮,談起彼時台灣鬧過錯認西西是台灣作家的烏龍時,彷若昨日。
無論是意外被啟蒙還是錯認,陰錯陽差之間也說明了六、七○年代因香港出版環境艱困,作家大多替報刊雜誌寫稿,卻少有機會集結成書,台灣成了香港作家作品出版發行的中心地。
除了書的出版,黃勁輝追著劉以鬯在國民黨在港反共刊物《香港時報》文藝副刊「淺水灣」作主編的線索(1960年到 1962年),來到台灣訪問詩論曾被刊在「淺水灣」的張默,原來,他在海軍陸戰隊新聞報社服務時,因為機構訂閱刊物的關係,讀得到從香港來的《香港時報》、《好望角》。其實,不僅僅是張默,大荒、朵思、葉泥、紀弦等詩人,學者魏子雲,新聞人吳心柳(張繼高),甚至是白色恐怖受迫害的畫家秦松、舞蹈家蔡瑞月,都在「淺水灣」發表過版畫與文字作品,一支台灣文藝偶像團體透過劉以鬯的引介在香港華麗登場。
劉以鬯作為編輯,還企劃、譯介了一系列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作品與文論,盧因寫給「淺水灣」的〈意識流小說的理論與技巧〉正是「意識流」第一次在香港刊物亮相。六○年代,劉以鬯作為香港現代主義推手,與台灣的現代派雖然隔著海,卻總像貼身跳著恰恰。
說起編輯工作,《1918》與《我城》都花了許多力氣讓劉以鬯、西西坐在編輯台後的身形顯影。劉以鬯在戰前中國就已經編過幾份刊物,1948年到港以後,只剩一枝筆,基本上都是靠替報社寫稿、擔任編輯謀生。50年代初期還一個人到陌生的南洋任總編輯(幸好在那認識了太太,而且是認識了一個月就說那你不如嫁給我吧,媽呀)。回港後,他維持日日生產一萬字連載小說送往不同副刊的生活,最多同時寫十三個專欄,還要兼顧處理稿件、排版、企劃等編務。寫《酒徒》時,他每天寫一千字就送去《星島晚報》,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近似工廠生產線的魔幻場景:小說家禁閉在斗室不斷產字,同時為不同報紙供稿,什麼稿都接,寫好了就趕緊請司機來取件立刻送往報社,完成工作後才到半島酒店吃下午茶犒賞自己,這就是多數香港作家努力在這個城市存活下來的狀態。
另外,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《中國學生週報.詩之頁》當編輯,雖然後來當小學教員維生,不過又提早退休,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強養活自己也養活寫作。七○年代先後加入何福仁創辦的《大拇指週報》、《素葉文學》,都是培養起香港本地創作隊伍的重要刊物。但西西在訪談中回憶當初編刊物,那是賠錢在辦哪,除了加入之初要繳費以外,編輯沒有薪水可領,替刊物撰稿也是無償。紀錄片中,西西寫作的書桌被瘂弦命名為他見過最小的書桌。何福仁在《像她們這樣的兩個女子》也談過西西的寫作空間,就是在廁所裡張開一張小摺檯,一屁股卡在另一張小凳子上就開始寫小說 [4]。
類似這樣的香港作家日常,我們也看到羅卡回憶早期文藝少女西西在《中國學生週報》上寫過好多影評稿。她雖然是法國電影新浪潮鐵粉,但在香港重視娛樂性的環境,任何電影影評她都要寫 [5];後來,西西有機會進入片場觀摩,還接下了西方經典劇本改編的任務。對於導演的提問,西西先是笑她改編的《小婦人》國外都已經拍過電影啦,不過就是抄過來而已;又自嘲不會寫劇本,和龍剛導演合作的《窗》把日常對話寫成了文藝腔,惹得整個電影院哄笑 [6]。但是,後來客座擔任台灣《劇場》雜誌編輯的西西,卻也用廢棄的新聞膠卷剪出一部實驗短片《銀河系》 [7],形式在當時是非常前衛的。
若說香港作家與電影的關係,劉以鬯小說《酒徒》就反映了香港電影界劇本荒,老闆與觀眾多喜愛把國外故事照搬來港的改編劇本、或者古典文學新裝的故事新編。而主角老劉厭倦了寫通俗小說賣文為生,打算改行寫電影劇本,卻被嫌太過藝術,不但一毛錢都沒拿到,最後劇本還被導演騙去以自己的名義拍攝上映。劉以鬯自己就把作品分成「娛人」、「娛己」兩種,西西也曾經與其他「嚴肅文學作家」一起為專出「三豪子小說」的出版社寫類型小說。
紀錄片慢慢拼貼出劉以鬯與西西的職業生涯,於是我們發現香港作家早就都是斜槓青年,藝術和娛樂的拉扯永遠都紮根在他們的創作日常。不過,若讀兩人的小說,也會發現視覺性的實驗是極強的:劉以鬯的小說拼貼得像一大張方塊錯落、色彩斑斕的報紙排版,而西西的小說有時候甚至看來像電影分鏡,你要從哪一場開始看起都可以,與香港小說家作品多以連載形式發表在副刊上有關。兩位導演也在紀錄片呈現形式的思考上與小說產生對話關係。
巧的是,《1918》裡,劉以鬯在鏡頭前像個孩子一樣,在已然擠迫的書房執著地拼黏、展示一組又一組模型街區、牧場;《我城》中,陳果特別找來香港模型藝術家,搭建西西居住的土瓜灣,重現櫛比鱗次的樓房,讓她在旁邊來回走動,最終露出孩童一樣的笑容。
我認為那是我印象中香港作家最香港,最令我動容的畫面。
生活總是各種窘迫,香港寫作者的執著雖然看起來過於傻氣,還有一點任性,但其實更多是太理解現實,有過挫敗,也許絕望,最後從現實裂縫中長出來仍有抵抗性的,透徹與淡然。
「爬格子是痛苦的,跳格子是快樂的。 」 [8]這是香港作家的純真,也是香港作家的複雜。
因此我貪看《1918》中黃勁輝特寫劉以鬯痴看他拼裝的模型牧場,滿臉都是心滿意足。又不顧太太阻止,對著鏡頭拿起人,拿起樹木,獻寶一樣像在說你看我造人我造樹呢。果然一拿起來,樹木碎屑灑落,太太要劉以鬯別管了放著吧,鏡頭還在拍呀,我們又見老先生嘖嘖兩聲,旁若無人,悉心地擦拭起他的模型來。
而我也貪看《我城》裡西西幾次一本正經談作品,或坐著等導演指示時,陳果把她小說中的人物造成巨大玩偶經過她面前,或乾脆穿上緊身蜜蜂衣進行訪談,西西突然迸出的,夏日煙花一樣的驚喜。雖然攝製過程和映後導演發言引起風波,但一如廖偉棠說的:「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,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。雖然這是個壞同學,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。」 [9]
不過,當西西領著鏡頭逛土瓜灣,突然,小說家消失在大樓轉角,我們看到鏡頭簡直變成厄夜叢林一般慌亂的晃動奔走,跑去哪裡了呀?然後,遠遠的,西西半個身體探出樓的另一側,惡作劇一樣,一聲不吭的笑。在那一刻,我好像又看到西西成為西西






